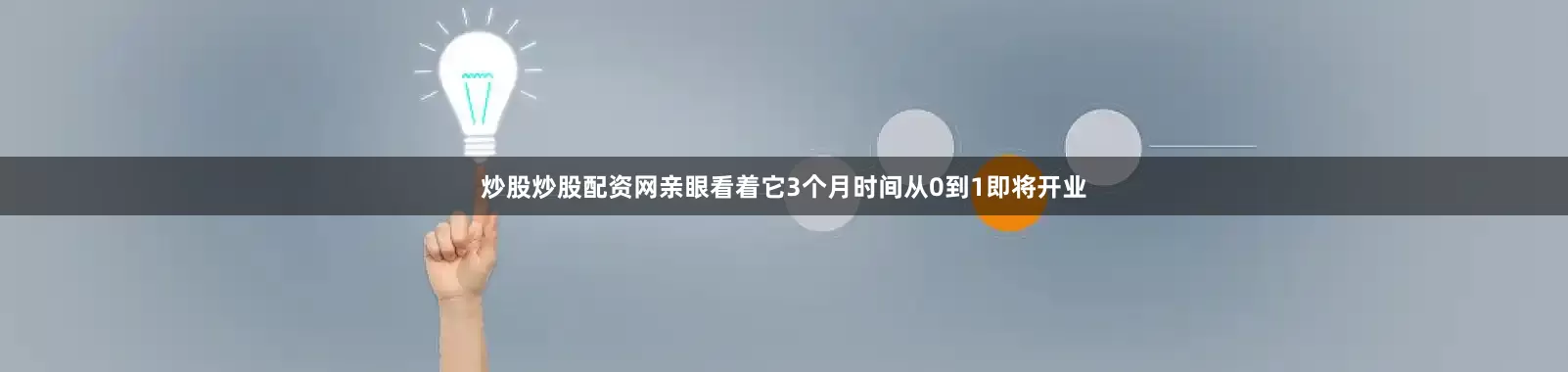一
元至元二十八年(1291 年),浙江义乌的药铺里,36 岁的朱震亨正对着《伤寒论》皱眉。
此时的他已考取秀才,却因 “家族十年内亡者十人,多死于热病” 而弃儒从医。
当时医坛盛行 “刘河间寒凉派” 与 “张从正攻下派”,医者动辄用麻黄、附子等温热药物,导致 “治热病反致阴虚火动” 的病例激增。
朱震亨目睹 “温燥药杀人如刀”,遂千里拜师,终成 “滋阴学说” 创始人,被后世尊为 “金元四大家” 之一。
二
据《元史・朱震亨传》记载,朱震亨初学医时,曾照搬古方治疗邻村富家子的 “高热烦渴”,用麻黄汤发汗后,患者虽热退却 “夜不能寐,舌红少苔”。
他请教老师许谦,对方点拨:“今人饮食厚味,情志易躁,与古人禀赋不同,滥用温燥,必伤阴液。”
这句话让他决心寻访名师,最终在杭州拜 “金元医派” 传人罗知悌为师。
展开剩余79%罗知悌起初拒之门外,朱震亨竟 “侍立于门外三日,雪深及膝不退”,终获真传。
罗知悌告诫:“医家多守‘阳主阴从’,却不知今人‘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’。”
朱震亨据此提出 “滋阴降火” 理论。
某次治疗一位 “咳血不止” 的官吏,不用传统止血温药,反而开 “知母、黄柏、生地黄” 等滋阴方.
众人皆惊:“此药性寒,恐加重虚寒!”
他却解释:“患者嗜酒厚味,实乃‘阴虚火旺’,非滋阴不能降火。”
三剂后,咳血即止。
据《格致余论》自注,他为验证药效,常 “自煎药试服,记录身体反应”,甚至因过量服用黄柏导致 “足冷三日”,仍坚持完善药方。
三
《元史・朱震亨传》原文
“震亨,字彦修,义乌人。初业儒,后弃儒习医,受业于罗知悌。其论病,以为‘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’,故治以滋阴降火为主,著《格致余论》《局方发挥》,力纠时医滥用温燥之弊。”
《格致余论》补充细节
“余见世医执《和剂局方》,凡病皆用温燥,不知今人阴虚者十居七八。如一富家子,病发热,医与麻黄汤,汗后热退而燥渴更甚,此阴液被伤也。余以‘大补阴丸’治之,方用黄柏、知母、熟地、龟板,滋阴降火,三日而愈。”
两段文献相互印证,既展现了他的医学革新,也揭示了金元医坛从 “重温燥” 到 “重滋阴” 的转变。
四
朱震亨将朱熹 “格物致知” 的儒学思想融入医学,主张 “治病先明病理,用药必穷其理”。
他在《格致余论》中说:“医道如儒道,不明理则误人,格物而后知病之本。”
这种 “理一分殊” 的思维,让他突破经验医学的局限,从哲学高度阐释病因,体现了宋元 “儒医” 的典型特征。
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收录大量温燥方剂,被后世医者奉为圭臬。
朱震亨却在《局方发挥》中直言:“《局方》乃治常病之方,今人体质已变,固守成方,犹刻舟求剑。”
这种 “不泥古、重实效” 的态度,与同时代王阳明 “知行合一” 的思想呼应,展现了宋元学者 “经世致用” 的精神。
朱震亨为方便贫民就医,常 “携药箱走村串户,遇贫者分文不取”。
《义乌县志》记载,他曾为救治瘟疫患者,“取自家田产换药材,全活数千人”。
这种 “以医济世” 的情怀,将儒家 “仁爱” 与医者 “仁心” 结合,成为后世 “儒医” 的道德典范。
五
一剂滋阴药的医学辐射!
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收录其 “大补阴丸”,称 “滋阴之法,始于震亨,后世医者宗之”;
清代叶天士的 “温病学说” 受其启发,提出 “救阴不在血,而在津与汗”,形成中医治疗热病的完整体系。
朱震亨创制的 “六味地黄丸”(由其方改良而来)至今仍是滋阴补肾的常用药,全球年销量超百亿;
现代中医治疗糖尿病、更年期综合征等 “阴虚证”,仍遵循其 “滋阴降火” 原则,临床有效率达 70% 以上。
义乌建有 “丹溪祠”(朱震亨号丹溪),医家入祠需立 “不滥用温燥药” 誓言;
其 “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” 理论被纳入中医教材,成为理解人体平衡的核心观念之一。
发布于:广东省实盘配资排行榜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